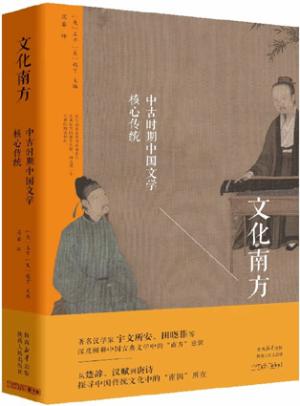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爱得太多的父母:14组家庭,20年追踪的家庭教育调查实录
》
售價:HK$
65.8

《
人偶游戏(东野圭吾竟然写过这种惊悚悬疑之作)
》
售價:HK$
65.8

《
自然、权利与正义(重思古典自然法 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根基)
》
售價:HK$
74.8

《
汗青堂丛书155·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
售價:HK$
118.8

《
企业家业保障与传承
》
售價:HK$
187.6

《
世界武器装备知识图解
》
售價:HK$
174.6

《
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
》
售價:HK$
2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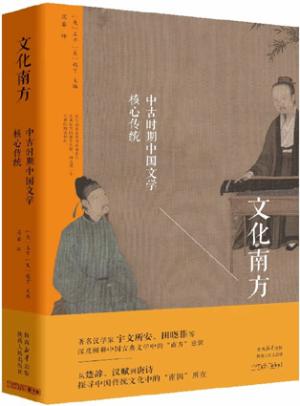
《
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
》
售價:HK$
70.6
|
| 編輯推薦: |
《日日夜夜》是苏联著名作家康·西蒙诺夫卫国战争期间写的一部反映苏军抗击法西斯德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中篇小说。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作品讲述了以苏军炮兵大尉沙布洛夫率领的一营指战员奉命渡过伏尔加河,进入被敌军围困的斯大林格勒,成功保卫了三座大楼的经过,表现了苏联军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
| 關於作者: |
作者:康·西蒙诺夫(1915 - 1979),苏联作家。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任《红星报》战地记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康·西蒙诺夫参加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作为毛泽东的客人来到北京,并以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译者:许磊然 1918 - 2009,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妻》《日日夜夜》《黑母鸡》《真正的人》《教育诗》《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毁灭》《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
|
| 內容試閱:
|
一个疲倦无力的妇人倚着小屋的黏土墙坐着,用疲倦得平静的声音讲述斯大林格勒是怎样被烧毁的。
天气干燥多尘。微风把一球球的黄土卷到脚底下。这妇人的脚被烧伤了,赤着,她说话的时候,用手将温暖的尘土聚拢到发炎的脚底下,好像试试用这个方法来减轻疼痛。
萨布洛夫大尉看了看自己笨重的皮靴,不由得后退了半步。他非常高大,虽然他的肩膀很宽阔有力,可是看起来总觉得他太高大,他那魁伟的、背微有些弯的体格,普通而严峻的面貌,有一种神气隐约令人想起青年时代的高尔基。
他默默地站着听妇人说话,一面朝她头顶上的那边注视,有一辆列车就在那边草原尽头的小屋旁边卸货。
草原后面有一带白色的盐湖在日光下闪耀着,这一切好像是世界的尽头。现在,在九月里,这里是离斯大林格勒最后的也是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再往前到伏尔加河岸就要步行。这个小城因为盐湖而得名为爱尔通。萨布洛夫不由得想起早在学校时代背熟的“爱尔通”和“巴斯孔恰克”这两个名字。以前这不过是学校的地理课。而现在,这个爱尔通就在这里:矮矮的小屋、尘埃、偏僻的铁路支线。
这位妇人老是唠唠叨叨地讲着自己的不幸,虽然她的话是听惯了的,可是萨布洛夫听了却突然伤心起来。从前他们从一座城退到一座城,从哈科夫到华路依基,从华路依基到罗斯索希,从罗斯索希到保戈恰尔,妇女们也同样地哭泣,他也同样怀着惭愧和疲乏交织的感觉听她们说话。不过这里是伏尔加中下游左岸的一片赤裸裸的草原,是世界的尽头,在这妇人的言语中含有的已经不是谴责,而是绝望,沿着这个草原再往前已经无处可去,在这草原上好几俄里以内既没有城市,也没有河流——什么都没有了。
“把我们赶到什么地方来了啊?……”他不禁低声说,最近几昼夜,当他从火车的加温车里怅望草原时所怀的满腔不由自主的悲哀都被压抑在这句话里。
这一瞬他心里非常难受,不过一想起现在他和边境之间的可怕的距离,他就不会想到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却想到他要怎样回去。在他的抑郁的思想里面,有一种俄罗斯人所固有的特别的固执,不许他和他的同志们在全部战争期间有一次认为“回来”是不可能的。
可是无论如何再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此刻在爱尔通,他突然感到这里就横着那个不能越过的界限。
他看了看匆促下火车的兵士们,他希望尽快地沿着这条满是尘土的道路抵达伏尔加,渡河以后,他就立刻要感到不会渡回来了,他个人的命运要在对岸才能和城市的命运同时决定,如果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城市,那就是说,他一定要死了,如果他不让他们占领,那么,或许他可以活下去。
可是坐在他脚旁的妇人仍旧在讲斯大林格勒的情形,说出一条条被炸坏的和烧毁的街道。萨布洛夫所不熟悉的街道的名称对于她却充满了特别的意义。现在被烧毁的那些房屋是什么时候的建筑和筑在什么地方,现在锯下来做街垒的那些树木是什么时候种植和种植在什么地方,她都知道,她惋惜这一切,好像她讲的不是一座大城市,而是讲她的家,那里面她所熟悉的属于她个人的东西都丧失了、毁坏了,使她非常痛心。
但是偏偏关于自己的家她一句也没有提到,萨布洛夫听她说话的时候,心里想,战争愈往下,惋惜自己失去的财产的人实际上愈是罕见。人们愈少回忆到自己扔掉的家,而只是固执地回忆到一个个刚被放弃的城市的时候愈多。
那位妇人用手帕的角拭去眼泪,用长久的询问似的注视扫视了所有听她说话的人,若有所思地、确信地说道:
“要花多少钱,多少劳动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