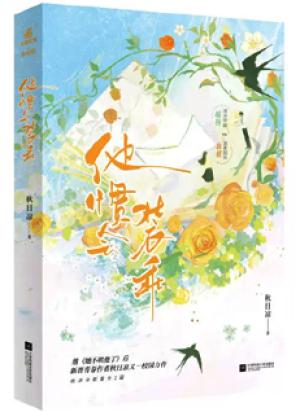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九色鹿·渤海国政治制度研究
》
售價:HK$
108.7

《
宠物造型设计与修剪(王欣)
》
售價:HK$
61.6

《
酱卤食品加工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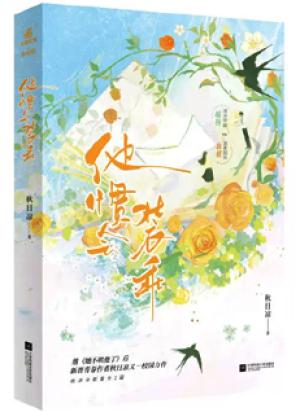
《
他惯会装乖
》
售價:HK$
52.8

《
从大繁荣到大萧条 1919—1939年美国社会生活史
》
售價:HK$
107.8

《
中西交通史 陆海书系
》
售價:HK$
63.8

《
图说新质生产力1:科技创新 落地化解读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精髓
》
售價:HK$
64.9

《
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医学人文丛书)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一部探究士人与权力互动的政治史
☆从封建迈向大一统的时代变迁切入,解读士人群体特性及其身份转变
☆揭示士人儒家化、宗族化、官僚化的历史逻辑
☆洞察士人仕与不仕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士人的政治选择,挖掘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仕”与“隐”(不仕)之间——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什么是隐士呢?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隐士形象,可能与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说的差不多,即“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隐士肯定有陶渊明,一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之风。但鲁迅对“隐士”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一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陶渊明中年以后有多次仕隐经历,最主要原因是因贫而仕。
|
| 內容簡介: |
“隐士”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然而隐士卓然出尘的形象,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慢慢成形的。在此之前,士人在仕与不仕之间的选择,时常因为文学的歌颂而逐渐扁平化,细节与脉络被埋没。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士原为低级的贵族,因此早期的士不会面临仕与不仕的问题。春秋晚期,贵族与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仕”才成为一种专业,士人才需要在“仕”与“不仕”之间做出选择。但不仕并不等于“隐”。先秦至两汉,经历封建制崩溃到郡县制大一统王朝的兴起,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士人群体从百家争鸣、士庶杂处逐渐儒家化、宗族化和官僚化。由于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人离开政治权力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从“隐逸”到“不仕”,再到“以不仕为隐”的过程。
本书通过爬梳《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史料,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不仕之士”做了全面统计分析。通过士人仕与不仕的人生选择,可以窥见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过程中,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以及士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
| 關於作者: |
|
白品键,中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现居桃园,任教于世新大学中文系。研究领域以先秦两汉时期的士人为主,包含学术思想如何与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以及士人如何沟通社会之不同阶层等。著有《士与汉代文化抟成研究——儒学、吏事与方术的揉合与实践》《潜夫论所反映之东汉流民问题》,学术论文十余篇,童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大富翁》等。
|
| 目錄:
|
第一章 “隐”与“不仕”之间:隐士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 1
前言:“隐”的研究探索 / 2
“隐”与“见”以及“仕”与“不仕” / 14
《庄子》书中有道之士及道家型隐逸 / 23
“不仕之士”:士人的政治抉择及其社会基础 / 49
第二章 争鸣与无迹:战国时期的不仕之士 / 54
战国时期“不仕”的多样性 / 55
战国时期的不仕之士 / 80
想象与现实中的战国不仕之士 / 93
第三章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秦至汉初的不仕之士 / 98
秦至汉初“不仕”的辨别 / 99
新时代的吏与仕 / 107
秦朝的不仕与蛰伏之士 / 122
西汉早期的不仕之士 / 137
小结:“天地一大变局”中的仕宦抉择 / 163
第四章 “修六艺之术,通万方之略”:武帝至王莽秉政前的不仕之士 / 171
西汉“不仕”的辨别 / 172
尊儒之后的不仕与隐者 / 176
不仕的儒生 / 185
儒生之外的不仕者 / 207
小结:西汉盛世不仕现象的变化 / 224
第五章 不仕王莽:两汉之际的不仕之士(上) / 232
两汉之际“不仕”的辨别 / 233
两汉之际的儒生与隐士 / 243
不仕王莽:儒生 / 261
不仕王莽:儒生之外 / 284
第六章 避乱与守节之间:两汉之际的不仕之士(下) / 325
两汉之际避乱隐居之士 / 326
不仕更始、公孙述、隗嚣、窦融之士 / 340
不仕王莽并不仕光武之士 / 361
小结:两汉之际不仕现象的发展与变化 / 380
第七章 仕途之外:士人的政治抉择与隐逸典范变迁 / 389
先秦时期:从伯夷、叔齐到侯嬴、朱亥 / 390
秦至西汉:从四皓到韩福 / 398
两汉之际:从龚胜到周党 / 410
结论:再论“隐逸”与“不仕” / 427
引用书目 / 431
|
| 內容試閱:
|
前言:“隐”的研究探索
“仕”与“隐”是中国士人一个长久以来面对的课题。作为一种人生抉择,“隐”往往被放在“仕”的对立面。在古代中国,凡拒绝入仕者,不论其拒仕的理由是什么、拒仕之后处于什么状态,大多被称为“隐”,或称隐士、隐者、逸民、隐逸、处士、高士等其他别名。从早期的文献史料来看,隐士之身份与形象起源相当早,《论语》中有荷丈人、长沮、桀溺等耦耕的洁身避世之士,至庄子则崇尚“虚而待物”的人生观,大量真实或虚构的隐士皆现身《庄子》书中。整体来说,隐士除了拒绝出仕之外,大多还拥有志节清高、安于贫贱、避世等特质,形成了中国士人的另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正式进入本书所要讨论的“不仕”问题之前,这里要先简单梳理一下关于“隐”的问题。隐士的传统其来有自,而且源远流长,乃熟悉中国史者皆知的事情,只是如要溯源,最早能推源至何处?“隐”的对立面是否就是“仕”?隐士有许多不同的样子,那么要具备什么要素,才能被称为隐士?
近代以“隐”为题的相关研究论著不算少,不过大多为通论中国隐逸文化的,如早期关于隐士的代表著作—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等。蒋星煜此书的序作于1943年,受到时代的影响,蒋星煜对于隐士有相当的恶感,可以说其写作的目的便是反对隐士,认为隐士来自个人主义与失败主义,因此其书末结论直称“勇敢地生活,不做隐士”。书中对于隐士有相当大量的负面批评,诸如“隐士这种自私而萎缩的人生是不合理的病态的人生”,“中国社会受了隐士‘孤高自赏’的流毒,所以人各行其是,苦难不能共当,欢乐不能同享,这是值得我们猛醒的”,等等。
蒋星煜此书主要陈述隐士文化的共通性,并以不同时代的个案作为例证,带有强烈的民国早期的时代主观意识。由于蒋星煜对古代隐逸文化颇多批判,因此无深入古代社会,依不同时代所面对的课题去探索“隐”的起源的企图。其多次以“巢父”作为古代隐士的开端,应该是受到了《高士传》的影响,多少有借此推远隐士起源的用意。蒋星煜于序中将隐士定义为:“‘隐士’的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礼,视富贵如浮云。”虽然蒋星煜以品格内涵来定义隐士,但行文中则明显将“不仕”与隐士做联结:“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国家的领袖?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哪一点值得我们喝彩和拍掌?却很少有人去研究。”除此之外,蒋星煜又在《中国隐士的政治生活》一章中,将隐士的政治生活分为“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以在野之名务在朝之实”“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三类,并说明:“隐士既一旦从政,即失去隐士身份,故于此不拟赘述。”诸如此类,皆可见蒋星煜实际上是以“仕”“隐”为基础来开展关于隐士的讨论的。
总而言之,《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企图通贯中国整个历史去讨论“隐”,却无法深入探讨“隐”或“不仕”现象的历史成因、变迁以及仕途之外士人的不同样子。
若要在各种通论古代中国隐士的书籍当中,举出一本较能挖掘隐士在各种情况之下的不同样子者,则当以胡翼鹏的《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一书为例。胡翼鹏在绪论中便标明了“隐士”此一称号定义之困难:“藏与不藏、仕与不仕、宗教与世俗,矛盾对立的行动和人生都可以被纳入隐士的范畴,因而,‘隐士是什么’似乎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简言之,胡翼鹏发现隐士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样子,无论是内涵与形式,或时代对于甄别隐士的标准都相当不同。因此胡翼鹏此书的主要问题在于讨论“隐士是什么”,而不以某个确切而简单的答案来定义“隐士”。
尽管如此,胡翼鹏在德行之外,仍不得不以“不仕”作为隐士的“本质根据”“根本特征”“关键立场”,认为社会辨识隐士的焦点,以及史家甄别隐士的特征,皆以“不仕”为首选,仕宦中人则被排除在隐士行列之外。整体来说,胡翼鹏以“不仕”作为隐士的某种基础,并且承认在此基础之上,隐士可以有各种变化,乃至某些个案可以跳脱于仕与不仕之间。
本书原则上同意胡翼鹏对于“隐”与“不仕”的关联性的分析,在后续的章节当中,所论述的“不仕之士”也有大量的隐士位列其中。然而《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一书毕竟企图在整个古代中国历史中挖掘“隐士”身份的建构模式,对于中国早期“隐”与“不仕”的起源、关联性以及更加细致的演变过程,无法有太多的着墨,因而此点则是本书写作可以发挥之处。
通贯整个中国历史来讨论“隐”,早期隐逸的溯源便难以深入。而以先秦两汉时期的隐士、隐逸为论题的,这里再举三本专书为例。其一是文青云的《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一书。此书有不少精彩的见解,对先秦至东汉隐逸传统的建立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对于政治社会的变化以及特定思想家的影响都有相当的着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青云仔细地爬梳了《尚书》与《易》中时常被后世引为隐逸起源的部分,认为其中并未发现隐逸思想。此外,借由《诗经》的相关讨论,文青云意识到世袭贵族与官职的关系,由于君王未必符合世袭贵族的理想,但他们又需要维护君王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因此世袭贵族若要拒绝履行个人对于统治者的职责,需要有其他理由。通过这样的推论,文青云认为“中国的隐逸真正始于孔子”,亦即由于孔子赋予了拒绝官职可依循的某种道德原则,使隐逸变成了可能,而隐士也因此出现于古代中国。
除此之外,文青云对于隐逸的定义也相当具有一贯性:他强调隐逸的关键要素是“自由选择”,而非“迫于环境的压力”。因此在文青云的理解中,拒绝官职是一种隐逸展现自我原则的表现,是重要而未必是绝对的因素。由此可知,文青云对于“隐”的定义全然是思想意义上的,而非生活形态或其他物质层面上的,也因此能将“隐”与“仕”从对立的层面解放出来,在论述上避免了许多顾此失彼的问题出现。
虽然如此,文青云的论述仍不得不面对几处不足。首先,文青云否定了孔子之前存在着“可以被确切称为隐逸的事情”,但其论证的方法往往是通过质疑史料的可信度,或是主观地认为其事迹“离奇”“相当不可能”而加以排除。即便是伯夷、叔齐、介子推等著名的早期人物事迹,乃至《论语》的记载,都被其排除在外。这种疑古过甚的态度,多少也带给了这本经典著作一些理念先行的阴影。其次,文青云的论述多半通过个案的例证来开展,对于时代的面貌无法有更具说服力的论证,也有待后续的研究予以补充。
其二是王仁祥的《先秦两汉的隐逸》一书。此书除去头尾的绪论与结论,正文四章分别探讨了隐逸的起源、先秦诸子的隐逸观、从春秋到新莽的隐逸与政治,以及东汉时期的隐逸风气。四章又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两章主要探讨隐逸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后两章则触及了隐逸风潮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王仁祥论述战国后期至两汉的篇幅不少,又广搜史料,将可见的资料并列讨论,对隐士的处境与思想都尽力做到同情地理解,堪称早期隐士相关研究的奠基之作。
王仁祥对隐逸起源的爬梳颇具启发性。他继承了文青云对《易》不具有隐逸思想的说法,却不排除《诗经》中已可见隐逸的存在,并引西周青铜器为例证,认为早在西周时期便有隐士出现。王仁祥还通过《诗经》中诗人所表达的忧愁与劳瘁,为封建贵族社会出现隐逸动机做出了相对应的诠释。
整体来说,王仁祥对于隐逸思想的出现以及对其社会背景的掌握,比文青云的论述更符合社会思潮渐进发展的面貌。
不过王仁祥在书中仍预设了“隐”与“仕”的对立,因此不得不将“隐”的讨论置于政治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
这将牵涉到一个文青云略有处理而被王仁祥轻轻放过的关乎士人的重大问题,即“仕”在春秋以前的世袭社会当中,是否能作为一种“自由选择”?如果作为世袭官员的贵族并无是否“仕”的自由选择,那么“仕”与“隐”仍然是一种对立的概念吗?
其三是蒋波的《秦汉隐逸问题研究》一书。蒋波以秦汉为断代来讨论隐逸问题,并且对于史料所见的“隐逸”做了相当程度的爬梳与整理,同时绘制了表格。虽然断代的区段以及选题的目标都与本书有所差异(本书论述“不仕之士”而非“隐逸”,主要讨论战国至两汉之际而非秦汉),但整体而言《秦汉隐逸问题研究》与本书的讨论范围相当接近。
整体来说,蒋波此书在秦汉隐逸方面可谓后出转精,对秦汉的隐逸现象有了相当细致且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以往研究较少的部分。蒋波不但将“暂时隐逸”的现象纳入讨论,对于隐士立足于社会的基础也做了初步的探索,包含第四章所探讨的隐士经济来源,第六章秦汉社会尊隐风尚的影响,等等。除此之外,蒋波费心收集了大量隐士案例,并完成了“西汉后期隐士统计表”“两汉之际隐士统计表”与“东汉隐士统计简表”三表,某种程度上为本书解决了部分基础工作问题。
蒋波此书虽以“秦汉”为断代,但又花了一些篇幅回顾了先秦的隐逸问题,且对于“隐士”有相当明确的定义:“那些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生或人生某个阶段选择不仕或暂时不仕,或曾经出仕为官却因故主动去官不仕的人。”蒋波显然将“不仕”与“隐”做了明确的联结,甚至可以说是以“不仕”作为“隐”的定义。如此一来,便与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 一书一样。这样的定义是否符合先秦社会的情况是一相当值得继续讨论的议题。
此外,虽然蒋波讨论秦汉隐逸现象时,能扣紧政治、社会的演变脉络,但回顾先秦隐逸现象时,并未追随文青云与王仁祥对于先秦文献所做出的还原解释(如《易》爻辞的解析),也未能针对先秦贵族世袭政治下的隐逸现象做出回应。此书以秦汉为断代,不能在回顾先秦的部分有过多苛责,因此代表了此论题还有更多讨论空间。
近三十年来关于隐逸的研究论文十分丰富,对于秦汉的不仕现象也多少有些论述。然而或由于其论述问题与本书颇有差异,或所论之完整度不如前述专书,故此处不费篇幅进行文献回顾。
综论历来对于“隐”的看法,大多数仍将其与“仕”对立,并以“不仕”作为“隐”的主要定义。然而就字义而言,“隐”为蔽、藏之意,而“不仕”是拒绝官职,二者不可互训。将其用于“士”,则“隐士”与“不仕之士”也不必然能等同,“隐”有隐于卑职小吏者,亦有隐于朝市者,未必不仕;“不仕”有畏罪自退而未曾藏身者,亦有居家却时时高论政事者。
本书主要谈论“不仕”,但由于其与“隐”之间有太多的牵连与混淆,不论是字义、历史脉络或具体的案例,都需要加以厘清区别,且理当从历史发展的源头谈起。
第一章 “隐”与“不仕”之间:隐士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隐”与“见”以及“仕”与“不仕”
不论是“隐”还是“不仕”,所描述的都是“士”的某种状态。首先必须厘清的是:“士”原为上古时期低级的贵族,能被称为“士”者,皆为本有封建政府职位者。顾炎武云:“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在职位与身份皆为世袭的封建时代,士并无所谓“仕”与“不仕”的问题。“仕”作为“士”的人生选择,春秋晚期才出现。在礼坏乐崩,封建阶级的固定性被破坏之后,贵族与庶民的界限才变得模糊,介于二者之间的士阶层大幅增加,使游士兴起,“仕”逐渐形成一种专业,并且有了“仕”与“不仕”的抉择问题。
“不仕”,如其词义所见,即没有在政府组织担任官职。若“仕”作为一种选择,此观念起源于春秋后期之后,那么在此之前既无所谓“仕”,自然亦无所谓“不仕”者。如前所述,传统上有“仕”与“隐”相对的说法,因此有不少以“不仕”来定义“隐”者。如果“不仕”必须出现于春秋后期之后,那么在春秋中期之前,是否已经有了“隐”的观念或具体行为呢?
如前文文青云所述,虽然其并不以“不仕”定义“隐”,但其否定孔子以前存在隐士这样的论点,反而符合了“仕”观念后起的历史脉络。然而文青云以近乎疑古的态度,几乎否定了包含《论语》在内的所有记载隐逸的论证方式,恐怕还有不少讨论空间。如《左传》中的介之推故事,便是一个文青云无法排除却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例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
以目前的学界共识来说,《左传》普遍被认为是一本可信的春秋时期史料,且在许多层面忠实地表现出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毁坏的历史。介之推的故事正好表现出几层意涵。第一,在介之推的理想中,扶持晋文公回国主晋祀,是理所当然的天意,这是贵族士大夫本分内的工作。“从亡”者通过扶持国君上位受赏,是“下义其罪,上赏其奸”,违背了介之推维护传统的理想,故称“难与处矣”。相对地,晋文公赏“从亡”之作为,正表现出春秋时期封建制度质变的样子,当“禄位”变成了士君子功劳之酬赏,从天命世袭当中解放出来时,如介之推这般传统价值的维护者,只好以“隐”来表达坚持。
第二,由于封建时代拥有某种名位不但是世袭,更是一种天意,因此介之推云:“主晋祀者,非君而谁?”而二三子之从亡也是一种职责上的必然,而非一种值得奖赏的功劳,犹如《庄子》书中所言之“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的君臣之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士君子并无退出官场居家而“不仕”的选择,因其“家”也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如有“难与处”的情况,便必须逃离一切,不但要放弃其名位,甚至连居家之位置、宗族之身份等,也必须一并抛弃。
换言之,战国以后士人可以通过“不仕”,依旧保留着自我的身份地位,乃至财产,但春秋时期,以及春秋以前的封建贵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放弃封建地位而“避世”。而原本依靠各种封建特权而生存的贵族,如抛弃了一切,往往也一并失去了生活的所有凭借,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此即介之推所谓“身将隐”或“隐而死”背后的文化意涵。
《左传》之外,《论语·微子》中的记载时代稍晚,但同样代表着封建价值毁坏的某种走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即使《论语》此章完成的时间可能晚至战国时代,然而孔子以春秋末期的历史角度向前评论早期人物,亦非极不可信之事。所谓“逸民”,何晏云:“节行超逸也。”皇侃则云:“民中节行超逸,不拘于世者也。”是取“逸”为拥有超出世道之外节行之意。朱熹则云:“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朱子说虽后起,但后多从其说,如刘宝楠引《说文》云,“逸民”即“佚民”之假借。钱穆先生亦云:“逸者,遗佚于世。民者,无位之称。”逸民是否无位?综合史料来看,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之子,柳下惠为鲁大夫,一说“柳下”为其食邑,虽三黜而不去,此三人是记载较为清楚的。虞仲疑有二人,一为吴太伯之弟吴仲雍,亦为吴伯,又称虞仲;另一为仲雍曾孙周章之弟,亦称虞仲,周武王封于周之北故夏虚。其余诸人虽缺乏史料,然历来亦疑诸位逸民皆是有位贵族。
以孔子的时代而论,既孔子申论古逸民之志行,则逸民皆为贵族,是较合理的推测。如虞仲者,既为吴伯,则不可谓之“无位”之民,又如柳下惠者,其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又岂能以“遗佚于世”称?因此所谓“逸民”,仍依何晏之说,解为“超逸”更为妥当。
孔子将逸民分为三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其一;“降志辱身”而言行中理是其二;“隐居放言”是其三。无论何种,都是身心言行与同时之世俗有所不同者。“逸”也就是“超逸”:在某种程度上逸于世道之外,坚定地采取自我所欲施行的道。孔子又云:“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正好表现出在理想坚持之下,封建贵族针对其君主或所处环境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反抗或不合作。
因此,世袭封建社会之中,虽然无所谓“仕”与“不仕”,但贵族却仍拥有各种不合作的选择,可以“降志辱身”地选择辟色、辟言,可“隐居放言”地藏匿自我,维持清高,更可如长沮、桀溺等这般,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封建秩序中,成为安于与鸟兽同群的“辟世之士”。乃至于如伯夷、叔齐或介之推这般,不但辟世、辟地,甚至到了无所可辟的地步,而以死亡为自我的某种生存理念作结。
由此可知,在春秋以前依其不同的程度,或志,或言,或行之不同于他人,而有所谓“逸”。在逸民当中有所谓“隐”,是更进一步的藏其身,匿其名,或抛弃、逃避原有之地位。在封建政治当中,“隐”的相对词当为“见”,或“显”。如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或前述介之推之“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等等。贵族贤者“不降其志”而“辟世”,即是“隐”,不必等待战国礼坏乐崩之后才出现。
“隐”具有隐辟之意,“不仕”则未必如此。司马迁记载孔子云:“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又记载孟子云:“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两大儒皆以修道立教为己任,孔子甚而主张“不仕无义”,可见孔、孟之“不仕”,在于求能行道者,故邦无道则去,毫无隐辟、潜藏之意。与此相反,孔子乃求善贾而沽之待仕者,二圣皆有强烈的以道明志用世之心,无论如何难以称之为“隐士”。
在社会流动较为停滞的封建时代,本有名位而辟逃之隐逸者,欠缺春秋后期之后周游求仕的选择,于是或入山林岩穴,或荷耦耕,形成后世对于隐逸的重要想象,亦即《后汉书·逸民列传》所言:“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战国以后,“不仕”与“隐逸”在意义上仍并非全然等同,如《礼记·王制》所载:“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此处之“不仕”,仅称其“不任大夫”之事,未必有隐居之意。
就语义来说,战国时代以后逃离名位之士,多半亦逃离了原本的仕宦之职,因此“隐”与“不仕”出现了较为具体且明显的共通性。但若更进一步区分,则各自仍有对方所无法涵盖的部分,“隐”的现象要比“不仕”来得早,其“志”则往往明确,以至于只要有隐蔽自我、逃避功名之意,即使有官职在身,亦可为“隐”。而“不仕”出现的时代较晚,在战国时代还伴随着“周游”的可能性,不仕于此,可求仕于彼,甚而必须更加努力地以著作、讲授、游说等方式“见”于世,以求得用而“显”。
以形式而言,“仕”与“不仕”在定义上相对比较容易,但“隐”的典范从伯夷、叔齐到战国时期成书的《庄子》之间,仍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