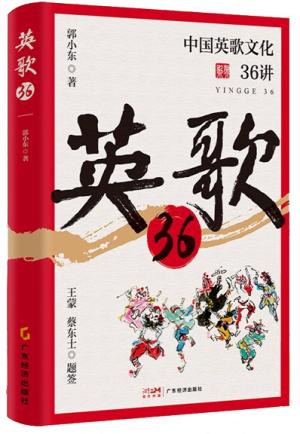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文心雕龙义证(全四册)
》
售價:HK$
349.8

《
国史大纲(上下册)(简体字版)
》
售價:HK$
107.8

《
长寿:逆转和延缓衰老的科学饮食(上下册)
》
售價:HK$
184.8

《
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40幅插图,深度还原安史之乱重要战事)
》
售價:HK$
151.8

《
亚伯拉罕的行李:中世纪印度洋世界的饮食、日用与旅行技艺
》
售價:HK$
129.8

《
中国历代文论要略(全三册)
》
售價:HK$
1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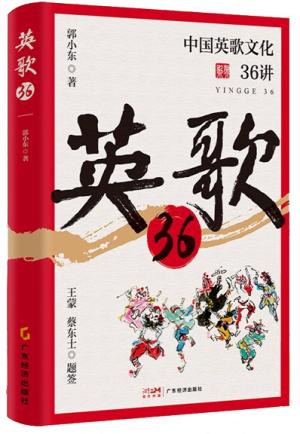
《
英歌36( 国家级非遗“英歌舞” 潮阳英歌文化)
》
售價:HK$
74.8

《
汪诘经典著作 时间的形状 相对论史话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师从名家,身为名师。作者李治安教授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1982年至1988年间,师从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攻读元史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现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名师。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典范。李治安教授以攻治元史著称,硕果累累。已出著作10余种,其中《元代行省制度》《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等,已是了解元代历史的经典之作。除了断代史之外,他还以贯通式研究获得阎步克等专家学者的赞誉,其相关论文(已收入本书)曾入选《历史研究》年度十佳论文、《<历史研究>六十年论文选编》等。
立足文本,会合疏通。宏观研究易流于概念名词的推理演绎,而李治安教授积极面对诸多史料的主次混存和繁复衍变,花大气力辨识并运用普适性的典型材料,综合考量其在“已然”和“所以然”逻辑链中的角色及与他者联系。虽然引入模式分析,但依然立足史料实证,尽可能在理论思维与文本实证的会合疏通基础上取得一家之言。
迎难而上,聚焦大课题。书中所收十余篇论文,系统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支配主导模式、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均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重点、难点和热点
|
| 內容簡介: |
|
李治安教授是元史名家,素以元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研究著称。近年其学术视野又扩展到更长时段的中古史探讨,力图将微观考据和宏观纵论相结合,尝试改变琐碎支离之偏失。本书收录了作者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的史学论文 11 篇。以贯通式大视野,重在厘清政治支配、南北地域、民族融汇三组论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各时期的表现,着力把握政治支配与地域差异、族群关系的错综交织或相互影响,抉发一家之言。作者秉持文本实证与理论思维并重,扬弃概念名词推演,通过多维度的融通探研,以新方法、新问题、新视角全面推进了中古史的再认知。
|
| 關於作者: |
李治安 著
李治安,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元史、中古史研究学者,元史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忽必烈传》《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等。
|
| 目錄:
|
融通古史 探索未知——代序
政治支配论
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
一、秦至西汉编民耕战模式的确立与鼎盛
二、北朝至隋唐编民耕战模式的复兴
三、明代编民耕战模式的最后“辉煌”
四、编民耕战模式的历史地位及局限
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
一、齐四民“通货积财”雏形及其与秦“军功爵”编民耕战的博弈
二、两汉“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起落浮沉
三、晚唐至两宋“两税法”“不抑兼并”与“士农工商”模式的定型
四、“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历史地位
试论元明户役当差与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
一、元代诸色户计当差的起源、定制及其在不同地区的实施
二、明代“配户当差”及“纳粮也是当差”
三、当差服役秩序与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
南北地域论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
一、第一个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
二、关于第二个南北朝存在与否的考察
三、“唐宋变革说”与第二个南北朝的发展线索
四、明前期承袭元制颇多与南、北两线索的整合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
一、元朝的北制本位与北制因素的诸表现
二、元统一后北制向江南的推广与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
三、明前期承袭北制颇多与南、北制因素的两次整合
四、结语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
二、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
三、5至16世纪江南在南北地域整合发展中的能动角色
四、余论
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
一、元朝统治政策与江南社会状况
二、朱元璋父子的个性政策与江南社会蜕变
三、“唐宋变革”视域下元、明江南政策的比较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
一、大运河保障漕粮北输和维护南北政治统一
二、大运河与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
三、大运河的时代局限与元明以降历史地位嬗变
四、结语
民族融汇论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
一、农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进程
二、后期的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和元“内蒙外汉”、清“内汉外满”
三、驳“崖山之后无中国”
四、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
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一、“中国”“华夷”释义与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
二、元代“混一华夷”的初次实现
三、明清“华夷一统”的曲折与发展成熟
四、余论
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
一、元明“华夷一统”为主及明兼用“中华一统”
二、清前期改称“中外一统”
三、清中期以降逐渐转换为“中华一统”
征引史籍文献与参考论著
一、史籍文献
二、参考论著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融通古史? 探索未知
——代 序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已被历史学者奉为圭臬。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突破政治史藩篱,注重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倡导“长时段”和总体史,流风至今不绝。拙著《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较多受二者影响。此外,南开史学“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优良传统,也是激发我思路的源泉。之所以冠名“三论”,即表明并非系统性论述,充其量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三组比较重要的问题,略抒己见,做一番融通古史、探索疑难未知的尝试。大致是研读史书之际提出一些粗线条的想法,供读者、同仁参考。
我探讨的第一组问题是“政治支配”。
一般认为,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是古代东方的通行法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干精髓。20世纪初叶以来,有关帝制国家政治支配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和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等,颇具权威性。鉴于帝制国家的政治支配延绵两千年,各王朝各时期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深究史料或采用新视角时,仍可能在某些内容和层面寻找到新的阐释余地,仍可能博采前贤之长而有些许的推进。
我觉得,秦朝以降虽难脱“家天下”的窠臼,但皇权官僚政治直接管辖百姓,一以贯之,最具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两千余年政治支配的要害。于是,我撰写《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和《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二文,尝试将历史的、逻辑的方法与模式分析结合起来,重点展开对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讨论。
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王朝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至西汉的鼎盛、北朝至隋唐赖“均田”“府兵”“租庸调”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不同凡响。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战”。其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本质又在于和郡县官僚制配套,构建直接役使百姓的国家农奴制秩序,进而为皇帝专制集权提供最大化的社会资源平台。该模式以授田暂时解决地主经济的“瓶颈”难题,充任皇权官僚政治与农民之间统制、隶属的“链条”,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延续发展和重大工程营造等,厥功甚伟。但“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及强制析产分户,往往带来“逃户”脱籍、人口与资源失衡等后果,又客观上助长君主及官僚的权力膨胀,或滥用战时体制,或强化徭役,进而酿成暴君祸害天下和官民极端冲突,增大帝国风险系数。其“公权力”被滥用等缺陷,又需要“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来寻求缓冲或出路。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作为帝制国家临民理政及管辖地主经济的第二种政策模式,肇始于齐国四民“通货积财”,中经两汉的起落浮沉,定型于晚唐至两宋。它主要在晚唐到清的多数时段施行,又以晚唐至两宋最为典型,“两税法”为其开辟道路,“不抑兼并”充任基本导向,实乃“唐宋变革”在临民理政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成果表征与最终胜利。其内涵精髓在于: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将身丁管控改为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不搞授田,不抑兼并,徭役及兵役或转变为差役雇佣,或基本消失,鼓励农商并重和藏富于民。四民较自由地致力于本业,自前而后的贵贱等级排序及相应管制不复存在,士人、富民又构成政治、经济两大支配势力。该模式较多祛除借重役滥税将“井疆耕耨之丁壮”抑为“国家农奴”之弊,较多祛除过度管制经济和妨害民营“造血”原动力之弊。但皇权最高所有、土地周期兼并、“权力商品化”和官商榷卖勾结等,基本沿袭耕战旧制,只能算是前者的变通而已。
我还专题撰写《试论元明户役当差与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剖析元明役法背弃两宋的进步,进而充任明编民耕战“最后辉煌”的基础性内容。这又算得上蒙古等北族入主带给“政治支配”的一份沉重遗产。
我探讨的第二组问题是“南北地域”。
据我接触的元明史、隋唐史等重要问题,几乎都和中原、江南、塞外等南北地域紧密相关。这也是萌发第二组讨论的缘起。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草原儿女游牧天地的塞外大漠,既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辉煌5000年的疆土故园,也是古代地域及族群互动交融的广袤平台。自古以来,我国疆域所在的东亚大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皆有万里之遥,地域、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族群习俗千差万别。观察5000年的悠久历史,全国或总体的视野固然重要,这也体现于以往古代史研究的主流话语及主要成果。然而,一味简单使用全国或总体的观察角度,有些史事往往难以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况且,第一组讨论中的“编民耕战”、“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及元明“户役法”等,似乎都离不开东西或南北地域联系的大背景。早在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桑原隲?藏、中国学者张荫麟等业已关注历史上的南北地域关系。傅斯年先生也曾说,东汉以后常常表现为南北关系[ [日]桑原隲?藏:《歴史上より観たる南北支那》,载《白鳥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52年,第387—480页。另参见氏著:《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载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8页。张荫麟:《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浙大史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0年;今据《张荫麟全集》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61—1771页。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1—232页。]。正因为如此,关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塞外大漠等南北三大地域板块相互关系的研究,就成为牵连中国古代史全局的重要问题了。
“南北地域”的探讨,由五篇文章组成:前两篇考察魏晋到元明1300余年间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第三、四篇探研江南居中角色和元明江南政策比较,第五篇则揭示大运河漕运命脉对南北社会的深刻影响。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一文提出,两个南北朝所造成的隔离与差异,直接影响中古以来的历史进程。恰恰在“唐宋变革”前后,历史发展是呈现南、北方复合状态而非单一。第一个南北朝、隋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线索而发展演化的。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南朝”“北朝”二线索的整合。中唐以后整合完毕,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第二个南北朝及并行的两条线索确凿存在。南宋承袭“唐宋变革”的成果,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趋势,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也作用显赫。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及明中叶以南制为主导等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此乃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
作为上文姊妹篇的《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进而认为,元朝统一后,国家制度层面的南、北制因素依然并存博弈。此时的北制,是指蒙古草原制度与中原汉法等混合物,南制则反映原南宋社会经济体制。由于北制因素过分强大,北制向江南的推移明显多于南制因素保留及北上渗透。朱元璋、朱棣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关系等交互作用,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占优势。明中叶后,南制为主导的另一次整合,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的轨道且得以升华。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主张,因北方民族两次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中原残破及两次南渡,5世纪以后的江南遂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推动经济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继续繁荣,厥功至伟。
《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的论题是:元世祖等实行南北异制,客观上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有所发展;明前期卫所军户、“均工夫”“配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触动极大,使江南几乎倒退至自然经济状态。元朝征服江南与宽纵豪富相“背反”,官场腐败与贫富悬殊相叠加,招致经济畸形和“官逼民反”“富逼穷反”。明初富民农商经济秩序被破坏及户役法南北通行,改变了江南延续近千年以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无几的“配户当差”。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因宽纵豪富和管制农商两种政策的更替,居然走上了畸形繁荣和锁国萧条的不同道路。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指出,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贡纳漕运及徭役物化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大运河有利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和江南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运河城镇和带动北方经济恢复,更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大运河利大于弊。漕粮海运与客商河运分类配合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漕,其滥用徭役,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我探讨的第三组问题是“民族融汇”。
在讨论“政治支配”和“南北地域”之际,我深感5000年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不仅是由不同地域子文明的碰撞整合而造就,也是由不同族群的交融合汇而造就,这两类造就又经常复合交织发生作用。可以说,各地域子文明和各兄弟民族的互动汇聚,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5000年辉煌。其间,塞外北方族群的南下,大多牵连或影响前述黄河、长江与塞外等三大地域板块相互关系及发展走向,更容易直接引发演绎出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融汇,甚而引致编民耕战模式的复兴或最后“辉煌”。于是,“民族融汇”自然成为第三组讨论的聚焦点。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主张,5000年来,“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辽宋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兄弟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体现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的历史主动性和汉、蒙、满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及其与社会经济互为交织的作用。
针对海内外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及汉族等56个民族间关系的迷茫,《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和《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二文,予以溯本穷源的历史学解读。首次提出秦汉至明清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分为郡县制单一式和囊括中土(概指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汉族等农耕区。书中“中土”一词内涵同此)、塞外的华夷多元复合式两阶段的新观点。着重阐明秦汉“中国一统”以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县官僚制管辖编民,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秩序和演进基础。元明清“华夷一统”形成了囊括中土和塞外的华夷复合式共同体。先有元朝制度、文化、族群的“华夷混一”,继而是明成祖争夺主导权未果及“华夷一统”说辞连篇累牍,最后是清统治者对“华夷”二字讳莫如深却有了较成熟的“华夷一统”建树。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升华。进而指出,“华夷一统”“中外一统”和“中华一统”,都是对元明清多族群复合共同体的话语转换,实体却始终未变。这类话语转换,对“中华民族”命题面世及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堪称阶梯准备。现代中华民族或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直接前身,就是元明清“华夷一统”复合共同体及其更新话语“中华一统”。
以上三组讨论,说来事出有因,也有几分遭逢际会。
197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因年届而立,颇珍惜读书的机会,课余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了《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隋唐部分,尤其是被司马迁《史记》深深折服,遂萌生了继续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意愿。我原本想报考先师杨志玖教授指导的隋唐史硕士,不料那年只招元史,于是听取南炳文先生的忠告,考入杨师门下。毕业留校任教,又在职攻读元史博士学位。我非常幸运的是遇上了博学卓识而又堪称学界楷模的好导师杨志玖教授,有幸得到先师的耳提面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及《行省制度研究》等。尤其是跟随先师学到从原始资料实证考据、钩沉索隐、建构新说之法。这确实令我受益终身。在此前后,我拜读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和《三论》,非常钦佩且偶有效法。在理论著述方面,我还粗略读过《资本论》第三卷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等。我曾承担刘泽华先生主持的“君主官僚政治”和“中华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子项目,又申报并完成青年项目“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受到探研古代史的初步锻炼。对兼治非元史的课题,杨志玖师抱宽容态度,我自己却心怀忐忑。一次,去看望蔡美彪先生,向他汇报没能专注元史,有些“不务正业”。蔡先生当即指点:这样做也是正业。承蒙先师的宽容和蔡先生的鼓励,我的心绪才踏实下来。20多年来,我招收元史和古代政治制度史两个方向的博士生,尤其在指导秦汉以降政治制度史论文过程中,委实是教学相长,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还参加“富民社会”“农商社会”等学术会议,与师友同好切磋交流。我觉得:主攻元史与兼治中古史(尤其是与元代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关联的部分),相得益彰,既可自元史切入去融通综观古代史,又能用古代史视野去鸟瞰理解元史。对克服元史研究选题单调,也大有裨益。
21世纪初,我年届花甲,打算在从事元史断代研究的同时,稍多做一些贯通性探讨。当时主要有如下考虑:第一,改革开放30年间,冲破“五朵金花”范式羁绊,断代史实证研究呈井喷式发展,但断代之间各自为战、沟通偏少等问题日渐突显,这无疑是史学继续繁荣的一种障碍。实际上,无论是社会经济抑或政治文化,往往会超逸断代,呈现诸多的上溯或下延。而那些超逸部分,或许就是古代史研究的未知或薄弱环节。既重视断代史基础性研究,又超越断代和融通古史,应是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第二,20世纪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大师前贤,兼具微观考据和宏观纵论的双重功底,既能“沙里拣金”,又可“鸟瞰四海”,堪称治史的垂范楷模。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其博通与横通的取径,同样是对吾辈的鞭策。第三,就历史学者而言,60岁左右学术积累有所增多,又兼自身专通“周折”及社会阅历,兼做贯通性探讨,既有可能,又是某种责任或义务。尽管史学发展日新月异,各断代成果层出不穷,贯通探讨常有风险,很容易“撞到他人枪口上”。但我愿意做一名探索者,在这条路途上,跌跌撞撞,蹒跚而行,又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磨砺?
海内外一些新方法和新研究动向,也曾给予我有益的思维启示或方法论营养。前述法国年鉴学派和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较多影响,以及傅斯年较早倡导“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第3—10页。],自不待言。哈佛大学杨联陞“擅长于融乾嘉考据、实证史学与社会科学为一体”[ 李大兴:《寻找杨联陞—被遗忘的学长》,《经济观察报》2017年5月8日。林风、陈思:《西方汉学界首位华人名家杨联陞》,《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4日。],施坚雅关于中国市场体系的核心与边缘结构说[ [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7—417页。],等等,是为新方法。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宋元明过渡说”[ Smith Paul & Richard von Glahn,eds.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参见张祎:《“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简介》,《宋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2期(总第42期)。],竺沙雅章的辽、宋、金、元“北流”“南流”说[ [日]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時代》,東京:講談社,1977年。另参见[日]竺沙雅章:《征服王朝的时代》,吴密察译,台北:稻乡出版社,2014年,第6页。],“新清史”学者所持“满洲”或内陆亚细亚自成体系说[ [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台北)2006年第2期。定宜庄、[美]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王明珂对华夏与其边缘共生互动的论说[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等,是为新研究动向。可以说,上述三组讨论,多半是在海内外新方法和新研究的刺激启发下的再思考,或者是对某些说法的回应批评。
涵泳其间,我有两点体会:其一,较多从唐、元两个断代切入,既瞻前顾后,又左顾右盼,着意厘清上述三组论题的来龙去脉及各时期表现,努力把握政治支配与地域差异、族群关系的错综交织或相互影响,尤其重视地域差异与族群关系两类考察相结合。通过多维度的融通探研,尽可能在中古史认知上有所推进。其二,不搞脱离实证的概念名词推理演绎。即使是宏观视野的论述,也要积极面对诸多史料的主次混存和繁复衍变,花大气力辨识并运用普适性的典型材料,综合考量其在“已然”和“所以然”逻辑链中的角色及与他者联系。即或引入模式分析之际,依然立足史料实证,尽可能在理论思维与文本实证的会合疏通基础上成一家之言。
说来也是巧合。杨志玖师曾撰《元史三论》,唐长孺先生曾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二者皆为论证精彩致密的传世之作。如今我却因政治、地域和族群三组问题的讨论,袭用“三论”之名。冥冥之中,又像是先师、前辈的教泽汩汩而至,灵犀有通。我袭用的不仅仅是“三论”之名,更重要的是希冀承袭、弘扬先师立足实证、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学术精神。果能如此,或许也是对先师当年精心教诲的最好回报和告慰。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为一名古代史研究者,不仅要还原千百年前的真实故事,而且要用21世纪的眼光去聚焦原创新题,追溯探索疑难未知,精心解析疑难未知。融通古史,探索未知,并非易事,肯定会遭遇不少波折或失误。即使偶有心得,抑或只是更接近历史真实,未必就是历史真实的全部,况且还会有新的未知。期盼同行师友和读者随时赐教,助我匡正失误,在探索古史未知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攀登前行。
|
|